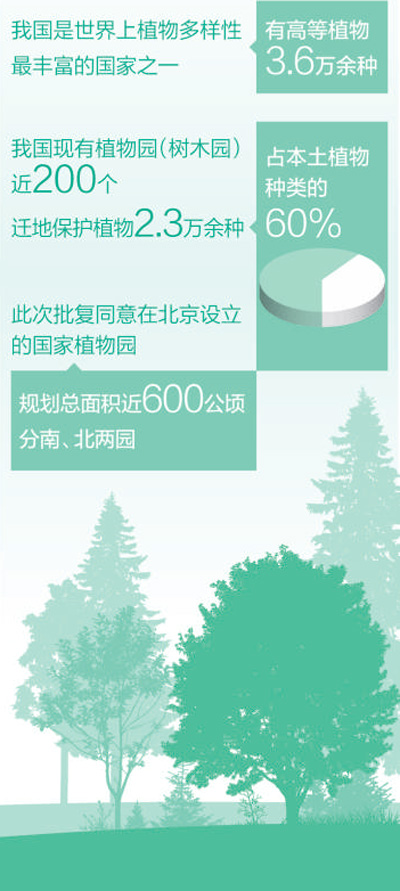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4月22日,第十一届春风悦读榜文化沙龙在杭州蝴蝶剧场举行。在春风悦读榜揭晓之前,作家毕飞宇、阿来、徐则臣、叶舟、路内、毛尖、乔叶、林棹、苏七七、刘洋、梁清散、戴浩然围绕沙龙主题“虚实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谈。文学可以为现实做什么?
 (资料图)
(资料图)
毕飞宇为何写作者希望以写作来完成对现实的独到表达?对此,毕飞宇认为,每一个人活着的过程也是奔向死亡的过程,伟大的死亡与虚无在等着所有人。虽然物理空间中的骨骼、肌肉、血液和律动都构成了我们现实的生命,但这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人本性之中的野心和贪婪自然会渴望挣脱物理空间和物理世界,便会通过寻找那些代表着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的东西、理念和情绪来进行自我表达,以此来完成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一生是一个X,最后我表达的还是一个X,我会觉得我的生命是失败的。生命是X,最后等我死的时候,大家通过我的表达发现,这个人给我们提供了X+,那我的生命就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在生命的本体之上,在物理性之上,在时间之上,在空间之上,它是有的,需要我们去找。”毕飞宇说道。“如果我们运气更好,我们所有的+加在一起,我们还能得到 ‘++’,这个+就是时代性; 如果我们运气更好,能力更强,我们还能得到‘+++’,那就是民族性;如果我们运气更好,才华更够,我们还能得到‘++++’,那就是人类性。”毕飞宇说。关于文学的基本道理,阿来觉得写作的基点在于对现实生活与社会的不满意,包括对自身生命状态与生活状态的不满意。不同于政治家会采取具体路径来修正现实,而作家修改自己不满意的现实与生命状态的路径则是进入到一个文字的世界,将他们对于一个理想世界想象与追求放到小说之中,也会在其中表达对现实的质疑与不满意。“如果其中出现一点理想主义的光芒,出现一点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更美好的期许,这又是使小说产生一点温暖与美好的路径,这种理想只有在文字世界当中得以呈现。”阿来说。
徐则臣谈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徐则臣说:”我们每个人是基于自己在当下所汲取的现实感和当下感,由此出发去重新看待那样的一段历史,所以每个人的写作它都有存在的价值。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我们讲故事的方法不一样,故事中透露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就是每一个作家基于当下的现实和他对时代的认知,以及对历史的重新打量,再次重构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一个作家重构历史或重新叙述历史的能力很重要。正如有句话说:“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历史的时代’。”而路内指出:“你总是去追求一个新的当下的时候,是不是会忽略掉某些其他东西,因为如果你将这个当做写作的唯一原则,会丢掉我们在写作中更丰富的东西。当我们在书写一切就是在书写当下,反过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当我们在书写当下,实际上也是在书写历史。这样一个反向的思维会让我们写作的目光更宽泛一些,看得也许可以更准确一些。”
关于历史与当下的写作,叶舟结合了前两位作家的观点。他说:“我们的写作肯定是从自身出发,我觉得所谓的‘历史’就是你写作的半径,也是你想象的半径。我们每个人今天的写作其实就是构成了明天的历史。”他接着表示,历史与当下没有必要分清楚,历史可能清晰地存在着,它是活态的,它永远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当中。
谈及文学对现实的干预程度问题,在徐则臣的理解中,文学干预现实有现实与文学两个层面。所谓的现实层面上,也就是文学与现实的呼应,文学直接地呈现现实、提出问题,无论是批判还是褒扬,文学与现实之间一定意义上可以划某种等号。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也是整个读者期待文学所能体现的干预现实的一种设想。“对作家来说则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干预现实。马尔克斯写过一部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我觉得这部小说做到了在文学意义上绝对严格地干预现实,它完美地体现了一个作家对文学中呈现现实的处理能力。”徐则臣说。
对于这个问题,阿来认为:“ 我们的文学理论当中一直是主张一定要干预现实的,但在这方面,我多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们从文学史的例子来看,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经典的流传到今天的作品,我们将它们作为干预现实的范本,或者是直接影响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这样一个范本。这些范本当然非常有力量,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诸如此类的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力作。”他认为虽然这部作品对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并未发生干预作用,但依旧可以成为文学史的经典。在这里,文学作为一种现实的范本在发挥召唤性的作用。这种召唤仍然在,因为每个人对于现实与未来都有所期待。
科幻为何变得如此重要?关于近几年的“科幻热”现象,刘洋认为,即使可能会存在一些时代与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任何文学小说的热潮肯定是由最优秀最顶尖的作品所带动的,这才是根本原因。他说:“假设刘慈欣小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开始写科幻,没有接触到科幻这个文类,现在中国没有《三体》和《流浪地球》这些作品,我想中国可能会有一些科幻热潮,但是不会像现在这么热。任何热潮本身还是要回到它的文本,它肯定会有一些优秀的文本出现,带动这些读者了解与喜欢这个文类。”
作为一名科幻编辑,戴浩然认为:“我能够感受到,一方面最近这几年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科幻创作者,他们的作品非常的强劲,比如《火星孤儿》和《不动天坠山》。这些作品与优秀创作者的出现,让科幻变得越来越兴盛,越来越繁荣,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逻辑。”
梁清散关于中国原创科幻文学的特点,梁清散说:“因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与教育方式下,写出来的科幻肯定是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里头。但是这个独特的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总结出来,因为各种形式都有,表现出来是百花齐放的一种形式。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自己的东西的内核在里头,这可能是相对来说统一一点的特点。”戴浩然对这个问题有另一层面的理解:“当下我们的科幻作者一方面继续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吸取智力上的愉悦感和材料来建构文本,还越来越愿意去挖掘和感知自己的内心世界,为自己的文学作品赋予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和情感价值。在我看来这是目前中国科幻已经越来越清晰的一种特色。”
在“科幻文学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这一问题上,戴浩然说:“通过科幻我会发现,一旦引入更加广袤的宇宙观之后,人类在地球上做的事情跟我们看似好像特别宽广的宇宙之间也产生连接。至少对我而言科幻它能够带给我们读者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与认知上的体验,以及跟世间万物强烈的连接感,抵达更加广阔的、大家过去没有感知到的世界。”
刘洋在刘洋看来,科幻其实是对技术可能性的一种书写,对我们未来可能有什么样的技术及其可能会带来的具体后果的书写。同时也是对所有的平行宇宙未来的一个书写,这个平行宇宙很有可能不是我们所生存的现实宇宙,但是它是按照现实的逻辑和法则来书写的。“科幻书写可能的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这些情况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也不出现。一旦我们知道它有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引起某种警惕。科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疫苗,当它注射到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之后,整个人类社会意识到有可能有这种东西的存在。当这个东西真的出现的时候,就有某种程度心理上的准备。”
当我们谈论女性文学,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当谈到生活当中遇到过的“性别问题”,毛尖说:“因为我的名字比较中性,第一次见到我的人有点诧异,但好像多少带一点点赞美式的‘原来你是女的’,口气里边包含着‘你的文章写得不是那么女的’。听起来好像是赞美,但其实它包含了对女性写作的一个整体的俯视。”
毛尖 苏七七对于这个问题,苏七七说:“从出生起,你就没办法从一个‘性别问题’中脱身而出,我们生来比男性要多面对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男性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跟女性感同身受的一个原因。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讲,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受到某种影响?这是必然的。就像生育,如果你生过一个孩子,那你的写作和你对社会的参与度势必受到影响。它会占据你非常多的时间和注意力,甚至你不得不在某一段时间中断它,或者保持一个很小的工作状态。这是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就像伍尔夫说的‘你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林棹认为,每一个创作者坐到桌边开始创作时,都有一个自己先天的局限和后天带来的局限,可能来自于性别,也可能来自于阶级和地域,或者创作者的某种过去。“一旦创作者占有了什么,就意味着他/她会失去一些什么。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不断地突破这些限制,不管是性别,还是语言、地域等,这是创作者的理想状态。”
乔叶关于是否有必要在中国当下文学作品中鲜明地彰显女性力量与女性主义的热点问题,乔叶说:“因为我是女作家,我的作品展现的是典型的女性角度。我写了这么多年,有时候会在心理上拉开一个距离。除了女性,其实会考虑更多的角度。男性和女性下边有一个更基本的人性问题。我写作的时候,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要考虑更基本的人性问题,从基本的人性问题出发的时候,有时反而觉得女性角度是一种限制,会将女性框到更小的地方去,这是需要警惕的。”而苏七七提到了李凤群的《月下》,她认为,这部小说没有完全将女性放到受害者的角色,女性在上半部是受害者,下半部是复仇者,这是非常有趣的对照。她还提到了黄昱宁的文学评论集《小说的细节》,在这本书中,黄昱宁从奥斯丁写到石黑一雄,还写到了奥斯丁、伍尔夫、门罗和阿特伍德。“我们可以在这一个作品序列中找到我们的思想资源,找到面对我们的自身处境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的力量。总之,在不同文体的写作当中,女性作者还是越来越展现了大家的努力与光辉的。”苏七七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标签: